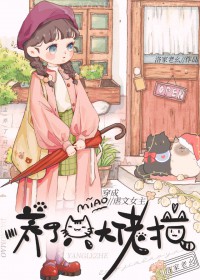分卷阅读165
同宁王并无关系’,什么‘自污名声’‘劳苦功高’......
他说的,是沈荷回?
然而皇帝却终究未能如她的意,神色如常,声音平静地告诉她:“是您待会儿要下的懿旨,内容儿子已然替您写好,您只需叫女官将您的印信拿来,在上头盖章
即可。”
太后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,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起皇帝的话,如同拨云见雾,有什么东西在心头豁然开朗。
从召安王进京,到公开同沈荷回的私情封她为皇贵妃,再到摆平安王叛乱,一桩桩一件件,都只是为了替沈荷回挣个好名声,将她捧成为国事忍辱负重的忠贞之女。
她从前还不明白,既然皇帝那样喜爱沈荷回,为何在面对宫里宫外对她的非议时毫无作为,不为所动,甚至隐隐有放任的趋势,如今却是懂了。
世人对沈荷回的争议越大,那么等这道懿旨公布之时,他们对她的敬佩便会越重。
他们会愧疚自己之前冤枉了她,从而对她越发敬重,将她欢欢喜喜地恭送上皇后的宝座。
这样用心繁琐的计谋,天下间,也只有她的儿子能想得出来,做得到。
“你早知安王心存谋反之心是不是,这一切,都是你设计好的......从头到尾,为的就是眼前这一道懿旨,是也不是?”
面对太后满脸的不可置信,皇帝只是微微颔首,说:“母后聪慧。”
“你———”
太后已经被震惊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嘴唇蠕动,怔愣了好半晌,才道:“你对她究竟是有多喜爱,竟舍得这样费心思,不惜把前朝后宫都给算计了进去,但凡稍有差池———”
“母后放心。”皇帝宽慰她,“儿子既然出手,自然就提前安排好了一切,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池,安王造反,除了少数跟着他的叛军,其余人,尤其是百姓,无一人伤亡。”
太后听见这话,脸上出现一丝讶然,未几,终于冷笑一声叹气:“你倒想得妥当。”
未几,她闭上眼,用力平复内心汹涌的心绪,将心头疑惑问出来:
“既然你想叫她
相关小说
- 夫君摔断腿后(1V2,NTR)
- 140052字03-19
- 漂亮小魅魔的被调教日常(囚禁 1v2)
- 漂亮小魅魔的被调教日常(囚禁 1v2)最新完整章节由网友提供。《漂亮小魅魔的被调...
- 46055字01-18
- 领证了,但不熟
- 1130220字05-16
- 不许觊觎漂亮寡夫[无限]
- 132252字05-16
- 穿成虐文女主后养了个大佬猫
- 236481字05-17
- 厉鬼巨佬都宠我
- 306879字05-16



![不许觊觎漂亮寡夫[无限]](http://www.biqushu1.cc/files/article/image/16/16622/16622s.jpg)